博鱼体育 boyutiyu 分类>>
谢志浩先生访问记:一所普通工科院博鱼体育- 博鱼体育官方网站- APP下载校人文传统的拓荒
博鱼体育,博鱼体育官方网站,博鱼体育APP下载

1985年我从辛集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,经过四年学习,1989年大学毕业“分配”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——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,1996年院校合并的浪潮中,河北轻化工学院与河北机电学院合并成为河北科技大学,同时,学校内部也进行资源整合,原来的政教室与德育教研室以及文史教研室,合并成为文法学院,2002年我申请调入刚刚创立的中文系。1985年到2002年,既有时间的绵延,也有空间的移动,还有学科的跨越,颇有沧海桑田之慨,陈远学友曾有一部书,叫作——《负伤的知识人》,可谓真实的写照。
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高考,是吧?1982—1985年高中就读于辛集中学,当时作为文科生,深受历史老师——赵庆仁先生的影响和熏陶。因为有位门生198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。受赵老师的激励,也等于说是受到那位学长的影响,热血沸腾,于是,第一志愿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并一举得中,当时,正值“文化热”,“讲座热”和“丛书热”,个体的启蒙与社会的复兴,同频共振,因此,“当身际遇”,异彩纷呈!因为大学四年灌注了强大的初始值,以后在河北科技大学以及前身——河北轻化工学院的所思所想,颇为另类,无他,惯性使然,想停都停不下来,三生有幸,我在一个好的时期,读了一所好的大学!
因此,仅凭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长一句话,我就来到了位于裕华路的“中校区”,当时叫河北轻化工学院。我去的部门,按理说也能发挥所学。谁能找到,一度『沦落』到想当政治课老师而不得!当时河北轻化工学院有一个“政教室”,顾名思义——政治教研室,约等于现在的『马克思主义学院』,正好有一位《中国革命史》老师,1989年到站退休,就空出一个位置来,谁能顶这个缺儿呢?殊胜因缘,我分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,就是为了顶那位老师的缺儿。
谢学友到了中文系以后,老院长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,都得怎么样?都得接受“科班”训练,此时“科班”显得异常重要。新中国的高等教育,它是建立在拷贝、继承红色苏联的基础之上,特别是我的母校——中国人民大学,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,它的模板是苏联。苏联的大学教育理念,重视“科班”——也就是专才教育。而欧美的教育理念,属于“万金油式”的教育,也就是通才教育,或者说是自由教育。苏联的“科班”教育——专才教育,某种程度上与“计划经济”相匹配,甘当一颗螺丝钉。
这就是所谓“科班”,中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,可以说异常重视“科班”,重视专才教育,准备让你当一颗螺丝钉。平常有一句话,经常挂在嘴边——专业人做专业事,这对不对?非常对!比如说外科手术,就得科室主任这个级别的专家。但,有些地方,未必如此。用人的时候,先问——你是学这个的呗?比如,要一位语文老师,不是学中文的,免谈!非要在这方面干,就不对。中文系只让学中文的来,其他的都要闪出去,给学中文的开辟一个“绿色通道”,然后,还要问是博士呗?是211呗?是985呗?大家看,这不就“卷”起来了吗!
当时,老院长说非“科班”出身的都得外出培训。此前,2002年,我“侥幸”成为副教授,二十三年过去,现在六十岁了,依然还是副教授,可以说“资深”副教授,将来会成为“永远”的副教授。由此可见,一所普通工科院校的副教授,多么不长进(一笑)。没有课题,没有科研,仔细盘点,著述九本——《那些有伤的读书人》《梦里犹知身是客》《叩问大学》《回顾所来径》《回望清华》《中国法政人素描》《中国社会学逸史》(一、二)《高王凌:特殊独一人》。这么多年描绘“中国学术地图”,愚钝如我,也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态有一个基本的估量,一个人,踏实,认真,努力,勤奋,一直都是副教授,大概,人的品性,不会太差。话说回来,《律师文摘》主编,中国政法大学《政法论坛》资深编辑——孙国栋兄夸赞敝人“著作等身”,“比博导牛”,心里那叫一个美!国栋兄见素抱朴,修辞立其诚!
谢学友在做自我介绍时,往往直接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,受惠于萧延中先生。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这段,只字不提。今天不妨跟两位学友开诚布公,说一说,北京大学中文系“访问”的是陈平原先生。陈平原先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便具有了很高的学术史自觉,这与我业余时间从事的“百年中国学术地图”,颇有契合之处。陈平原先生的同门师兄弟呀,像钱理群先生、温儒敏先生,各位学友都并不陌生,不是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的几位作者吗!
访学归来,担任一门课,现在已经没有了,大家也就不知道了——《人类学》。谢学友之所以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路径,其中一个机缘就是咱们中文系当时课程表里面有一门课——《人类学》。我认为现在全国中文系亟需开设的一门课便是——《人类学》,一方面或许由于自己曾经开设过,颇有心得体会,另一方面,中文系既然要跟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,就要懂得各种各样人的那种心情,心灵要有所交会。其中最为受益的学问,就是《人类学》。同时《人类学》也是一个学科群落,昨天晚上跟两位学友分享《中文与史学及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互动研究》时,曾有所论述,不再赘述。
1985—1989年,大学四年,听过沙莲香老师的《社会心理学》和李路路老师的《社会学概论》,更有意思的是,不止一次听过郑也夫先生的讲座,这样,慢慢接近社会学,后来,“社会学”与“学术地图”双向奔赴,交汇点便是费孝通先生,每一位学界老辈都是一部史书,费孝通先生身上刻画着中国社会学的“年轮”。2004年费老奔赴“九五之尊”前夕,我写出《开满鲜花的田野——播种者费孝通先生》,2005年4月24日,费老辞世,此稿发布在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。2019年河北科技大学招收社会学研究生“黄埔一期”,很自然,我受聘担任《中国社会学史》的课程。一位中文系老师,手伸得很长,占据一块社会学的“领地”,也难怪,中文系的老主任在介绍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风格时,直截了当说——谢志浩老师的学术专长是社会学。
哎,造化弄人!自己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本科学位,咱们学院2001年设立法律系,却不能在法律系任教,这也怨不得别人,谁让自己学的是“党史”呢!明明在社会学领域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,却也没能在社会学系教书育人。其实,中国新闻史,我也能插上一手,因为,不仅大学期间听过中国新闻史巨擘——方汉奇教授的讲座,而且也愿意理解老先生的当身际遇、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。无他,描绘“学术地图”既久,触类旁通,四处生风。咱们学友,听我一句话——每一门学科皆长在老辈学人身上,而非“课本”和“教材”里边,不能本末倒置。
承蒙李克荣院长器重,最先开设了《中国传统文化》选修课,《西方文明简史》忘了何时所开,也属于选修课。后来,《中国传统文化》由全校选修课转型升级为中文系必修课——《中国文明导论》,《西方文明简史》由全校选修课转型升级为中文系必修课《西方文明导论》,这是我在中文系的两个抓手。中文系最近在传达学习新的国家质量标准,这两门课好像均不在国家质量标准之内,也就是说,极有可能“人退课亡”。要是没有两位学友的访谈,差一点忘了,自己还上过一门《文化社会学》课程;另,一位同事外出读博期间,还替这位同事带过一学期的《古典文献学》课程。
1989年8月4日来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——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报到,此后的岁月,面临的最大问题,不是“安身”,而是“立命”。相对于“文化中心”北京而言,石家庄可以说是“文化边陲”,其实,经历剧烈的“文化冲突”,害怕患上“文化失语症”,就想拥有一些可以有共同话题的朋友,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,切磋学术,砥砺品行。这个“共同体”,利用业余时间,交流读书与思考,俗线年,正式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称——“席明纳”。
此前,从1989到2004年前后十五年,算得上“席明纳”的“史前时期”——没有“席明纳”的称号,但,照样与学友互动和交流,最为典型的就是与陈远学友漫谈百年学人。2004年拥有了正式名称——“席明纳”,从2004—2025年的二十多年,中间也曾风光过,还大张旗鼓地举办“席明纳”二十年的庆生活动,当然,也非一帆风顺,一度还颇为艰难。“席明纳”一头一尾,特有意思。“一头”指的是我与陈远学友聊学思脉络,“一尾”指的是我与焦浩楠学友聊当身际遇,均属于“二人转”,其乐无穷。
“席明纳”还是“连环套”,“席明纳”套着“席明纳”。杨云龙和李云飞两位学友,与陈远学长一样,皆来自工科,杨云龙学友来自环工学院,李云飞学友来自机械学院。大学期间,两位学友先后进入“席明纳”,杨云龙学友在中区完成学业,李云飞学友在新区的四年,图书馆还是没盖起来。难能可贵的是,杨云龙和李云飞两位学友均能“以仁心说,以学心听,以公心辨”,又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,做事干练,踏实认真,坚韧不拔。三观一致,思想相通,与谢学友颇为投契,毕业之后与谢学友既亲又近,堪称“席明纳”的“三驾马车”。迄今为止,谢学友九本著述中的七本,包括书稿结构,篇目构成,文章润色,文字校订,皆流淌着两位学友的心血与汗水,真正可以说是背靠背,肩并肩,手牵手,心连心,合作无上限。
我开设《中国传统文化》选修课,这得益于老院长李克荣教授。回首来路,饮水思源,哪些人曾经提点过自己,不应忘怀,也不能忘怀。郭德纲先生有一句话,一个人三分能耐,六分运气,还有一分是贵人提点,大概其,古今中外,概莫能外。这个很重要,这就是伯乐与千里马,这里边的道理很简单,大道至简。那个时候,我开设《中国传统文化》选修课,然后是《百年中国大学史》选修课,再后来,才是一度名声在外的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。《百年中国大学史》和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合,最后,《百年中国大学史》合并到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里边儿去了。
一些学友弄不明白,为什么我的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,老爱聊民国期间的大学校长、大学教授与大学学生,绝非偶然,这不是偶然的。别看那个时候兵荒马乱,但是,大学像大学,图书馆像图书馆,校长像校长,先生像先生,学生像学生,都像那么回事儿。也就是说,兵荒马乱并没有打散中国学人骨子里的精气神儿。不信的话,试着了解一下北大蔡元培先生、了解一下清华梅贻琦先生、了解一下南开张伯苓先生、了解一下复旦马相伯先生、了解一下浙大竺可桢先生,这样的先生多了去了,宛如平常一段歌。
2007年秋季,我好像还开过一门“空前绝后”的《大国崛起》选修课,咱们学校新校区是2006年建成并开始入住,第二年,2007年秋季教育部就进行教学评估。不少开设选修课的老师,偃旗息鼓,避其锋芒,干脆暂停一学期选修课,导致一千多同学,没有选修课可“选”,选不了课就获得不了相应的学分。教务处一位负责选修课的职员跟我说:谢老师,您把一千多位学生“接收”了吧!当时,我的选修课十分饱满,又不忍心一千名学友没有学分,就勉为其难,“接收”过来,针对这些学友,急中生智,开设了一门新课——《大国崛起》。讲课地点是新校区最大的教室——讲堂群202,两个头,此时,我才弄明白,讲堂群202可以盛得下640人,当时收音不好,音量小了,后排学友听不到,音量大了,前排学友吓一跳。
《大国崛起》选修课的开设,虽然是临时抱佛脚,也有自己的思绪和考量,总而言之,我所秉持的旨趣与钱乘旦先生不尽相同,和而不同吧!记得《大国崛起》政论片一经播出,引爆舆论,众说纷纭,我为此发愿编了一本《〈大国崛起〉争鸣集》,兼收并蓄,争取把各方意见充分吸收进来,同时,不经意间,也为临时开设的选修课提供了一个文本。刘军宁先生凭借深厚的政治学底蕴因而在这场争鸣中表现十分抢眼。看得出来,刘军宁先生试图把讨论引向深入,坚决主张——中国亟需一场文艺复兴。略感遗憾的是,刘先生的良苦用心没能得到认可,二十一世纪第一场『国运之争』,浅尝辄止,匆匆结束!
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近代文明史,尤其是在欧洲历史上,堪称推动文明前进的两大枢轴。文艺复兴发现了“个人”,宗教改革形塑了“国家”,也就是说“个人”和“国家”应当是“双向奔赴”——“国家”的力量十分强大,但是,“个人”没有力量,“大国小民”,不能充分发挥个人潜能,出现不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自由组合,“个人”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,“国家”终会走向失败;另一方面,“大民小国”,军阀割据,互相征伐,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,“个人”力量再强,不能形塑一个稳健的制度框架,“国家”也可能面临崩解。
还有一门选修课——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,一直开到2020年的疫情之前。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虽然并不需要延展着费孝通先生的当身际遇,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而开,这门课,最能体现敝人的社会关切。算下来,开设与社会学相关的课程,先后有《人类学》、《文化学》、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、《文化社会学》、《中国社会学史》,竟然达到五门之多。各位学友,或许有所不知,社会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消,前后近三十年。以至于1979年社会学恢复之后的二十多年,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前,一直都是敏感学科。社会学人畏畏缩缩,难以大展拳脚。我开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并不希望中国涌现大量社会问题,初心是想让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。许多社会问题,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甘当鸵鸟,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吗?!比如火车站如厕,一度并不免费,两位来自河南的汉子,杠上了铁路部门,最后,火车站上厕所,全国才免费了。
海淀路三十九号院,得遇恩师萧延中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诸位老师,实在铭感不已。这个教研室别开天地,另辟一家,擅长从思想史的角度,打量百年中国史,这是只能在政治史内部打转转所远远不能及的。桑咸之先生讲乾嘉学派,程歗先生讲义和团,林茂生先生讲民初思潮,萧延中先生讲新文化,闫润鱼老师讲三十年代政治思潮,皆一时之选,启人心智。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,久而久之,成为大学四年读书生涯的精神港湾。不愿意上其他教研室老师的课,之所以没有离开党史系,还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拯救了我,颇有再造之恩。
十分感念两位学友,促使我第一次提出形塑“百年中国学术地图”的五股合力。至于“学术地图”,不少学友听起来觉得有点意思,但是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简而言之,“学术地图”约等于各个学科“学术史”的多兵种合成演练,但是,它又不是纯正的“学术史”。“学术地图”,容易让人望文生义,给人感觉,眼前平摊一张地图,有的地方还有标注:这座城市有哪几位著名学者,那座城市有哪几位著名学者,不是,它是一个历史图景,某种程度上是有着一定的“纵深”的历史学术地图。
第二代的话,大部分受到了比较系统的、完整的“西学东渐”的这种教育。这一代产生了不少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泰斗、宗师和某某学科之父。比方说李济先生——中国现古学之父,赵元任先生——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,赵元任先生的友人——李方桂先生,这是“非汉语语言学之父”,为什么好多近代学科之父多为清华学人呢?无他,冯友兰先生说清华是一座国耻纪念碑!这是一座由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而建立的学校,清华人勿忘国耻,振兴中华!第二代的整体特征是『发凡起例』,因而产生这个学科的代表作,天设地造,殊胜因缘,清华“扎堆”产生泰斗和宗师。
清学研究院,陈寅恪、赵元任和李济三位先生均属“文化地标”,三位先生均曾在哈佛大学留学,赵元任、李济两位先生哈佛博士毕业。赵元任和李济没有陈寅恪的道行,只好一步一个脚印,最后取得博士学位。陈寅恪出身于贵族之家,深谙“游学”之理,出于求知的乐趣,满足好奇心和想象力,这么些年来被塑造成神一般的人物——别人是为了“学历”,陈寅恪是为了“学问”。陈寅恪先生在很多方面,都很令人佩服,比如提出“独立人格”和“自由思想”;比如,眼睛废了,自强不息,著述不辍,还在那里撰述《柳如是别传》。但是,陈寅恪的故事,放到旁人身上,就可能出现“双标”——比如我本人,英语不行,很早就断了读硕士的念想,此时,若是有人把我夸到天上——谢志浩为了“学问”,放弃“学历”,这时,我听到了,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。
陈寅恪先生的著述风格,这与没有读硕读博因而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,大有关联。李济和赵元任著作里面有一整套的科学法则,陈寅恪先生的著述里边,靠猜测,靠臆想,颇不少,依照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说法——所谓真了解者,必神游冥想,与立说之古人,处于同一境界,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,表一种同情。这样看来,陈寅恪先生似乎并不属于胡适先生所推崇的“汉学”,而是独辟蹊径,既不是考据派,也非义理派,而是“神游冥想”。
曾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赵元任先生是“现代汉语学之父”。赵元任先生天赋异禀,才华横溢,堪称百年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,古今贯通,中西汇通,文理融通,说的正是哈佛毕业的竺可桢,赵元任这样的大家!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“开山”,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这方面的学术,“先生之学问,或有时而可商”,陈先生的学问,可超而不可越,咱得知道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曾经奠定学术基石。魏晋南北朝不可解的事,本来就多,学术奠基人陈寅恪先生靠猜测和臆想,来破解魏晋南北朝历史之谜,倒也挺对症,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说法,依靠诗人之“神游冥想”。高王凌先生曾经在《超越“史料学派”》一书中专门探讨——史学研究中站在“义理”和“考据”之外的第三派,不妨称之为“神解精识”。高王凌先生的“神解精识”与陈寅恪先生的“神游冥想”,颇有相通之处,只不过,高王凌先生的“神解精识”偏向理性,而陈寅恪先生的“神游冥想”偏向感性。
第三代比方说河北乡贤——张岱年先生,还有钱钟书先生、费孝通先生、季羡林先生,不都是第三代吗?清华校史权威黄延复先生认为,清华理学院先后两位院长——叶企孙和吴有训领衔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大厦。清华学人古今贯通,中西汇通,文理融通,薪火相传,开拓进取,同样奠定了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根基,细究起来,张岱年,钱钟书、费孝通和季羡林,皆与清华有着殊胜因缘。钱钟书和季羡林先后毕业于清华外文系,费孝通清华社会学研究生毕业,抗战期间,钱钟书和费孝通曾任教于西南联大,抗战胜利后,均任教于水木清华;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,无奈,受不了罗家伦校长的“强迫训练”,转投北平师范大学,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后,任教于清华哲学系。清华出人才,这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群体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第三代往往出生于1911年前后,再加上20年,这就到了1931年“九一八”,生于忧患死与安乐,这是第四代之处境。不妨用杜诗的特征来形容第四代——沉郁顿挫,第四代诞生了颇多社会主义红色学统狙击手。1949年以后,毛公是集道统、政统和学统于一身的人物,“三美俱”,觉得胜券在握,所以亲自部署,亲自指挥,主动发起了向旧学统的开战。比如说对《武训传》的批判,对俞平伯的批判,对胡适的批判,尤其是从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,就可以看得更加通透。毛公明白,建设社会主义新学统,依靠老一辈学者,那是万万不能的,只有发现『小人物』,启用一代新人,因此,第四代的很多学人,无一不是行走在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口浪尖上的“刀锋战士”,故称之为“红色狙击手”。
经济学界与江平先生同一辈分的吴敬琏、厉以宁,当身际遇要比江平先生好多了,吴敬琏因为根正苗红,受到组织的信任,一度成为各种写作组的种子选手,厉以宁则由于右倾,枯坐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,过着翻译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寂寞生涯。一九七八年以后,吴敬琏与厉以宁,不鸣则已一鸣惊人,坊间从“吴市场”和“厉股份”的称誉,不难想见两位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所曾发挥的独特作用;国际政治学方面,一对卓越的“学术夫妻”——陈乐民、资中筠,堪称“学科地标”,陈乐民先生2009年过世了,资中筠女史还健在,2025年恰值“九五之尊”,这都是第四代之中的佼佼者。
同时的话,我在“百年中国学术地图”中,日益对1942年左右出生的“老五代”,产生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。什么叫“老五代”?大体是1961年到1966年五年之间大学毕业生。刘梦溪先生,俞荣根先生,还有2023年去世的冯天瑜先生,我认为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“第四代半”。这个“第四代半”的提法,刘梦溪先生不是那么认可。刘梦溪先生曾经主持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,对于百年中国学术的渊源与流变,学者的断代和分期,均有自己独到的看法,这一点,很难轻易改变;俞荣根先生有开阔的胸怀,欣然接受“第四代半”的提法。俞荣根先生为一位从事法律文化史的“大师兄”祝寿时说到——“河北科技大学的谢志浩老师认为我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四代半”。
中文系诸位学友,千万不要把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合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一书“固化”在所能呈现的填空、选择、辨析、简答、论述之中,可不是那么回事。要尝试着触摸一个学者的体温,体会到作者脉搏的跳动,进一步体察一位学人的“当身际遇”、“学思脉络”和“心路历程”。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!不能见到一本书,总是先问:这是“题”呗?一本书能出成题,就有大用,不能出题,就了无用处,如此实用主义,实乃人文教育之巨大悲哀。
民国时期意识形态体现在学术领域,就是以胡适先生领衔的,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作为先锋的“新汉学”学派。他们秉承清代的“朴学”——乾嘉学派,古今贯通,同时的话,因为身处西学东渐的时代,还有兰克史学的熏陶,中西会通,古代和西方的双重因素,形塑了民国时期的“新汉学”。我们知道,民国时期,政治上动乱,军事上纷争,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,以至于主旋律不能保持一枝独秀,也只好放任多元化。这样,以范文澜先生、郭沫若先生、翦伯赞先生、吕振羽先生、侯外庐先生,五位先生领衔的“新宋学”学派,就有生存壮大的土壤和水文。1949年以后这个“新宋学”指的是马克思主义。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,指导思想不是这个吗?
“宋学”讲究义理,“汉学”讲究考据,沉潜者尚考索之功,高明者多独断之学。不难发现,只要搞“宋学”的,不管“老宋学”还是“新宋学”,往往非常高明,因为敢于论断;反之,凡是搞“汉学”的,不管是“老汉学”还是“新汉学”,往往非常胆小,因为不敢论断,别看手中有那么多资料,胡适先生有言——“有几分证据,说几分话,有七分证据,不能说八分话”。不敢论断,胆儿小。记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彭明先生在课堂上常说,做学问,就要坐得住,还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,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。范文澜先生当年在北方大学,以及后来的华北大学,确实经常强调“坐冷板凳”。现在,终于找到出处了,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”,这副对联出自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。这在强调证据方面与胡适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,范先生就中国社会性质,历史分期,勇于论断。最合适的就是义理、考据和辞章“三美俱”,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《中国文明导论》课程以及它的前身——《中国传统文化》,曾经用过冯天瑜先生《中华文化史》,中间经历过自由发挥的“无课本”阶段,最后,选择梁漱溟先生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作为本子。梁漱溟先生并不以纯正学者形象示人,但是,梁漱溟与毛公一样,属于百年中国史上,集道统、政统和学统于一身的人物。尤其有意思的,梁漱溟先生的“学思脉络”和“当身际遇”密不可分。梁漱溟先生和梁启超一样,长期游弋于政学两界。读梁漱溟先生的书,不知其人,可乎?真的不可以!因此,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前面二十节课,不是用来讲解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理念和哲学内蕴,而是,细聊梁漱溟先生的生平遭际和当身际遇。一言以蔽之,梁漱溟的“朋友圈”——梁漱溟的尊人外,多来自政学两界,梁济先生,蔡元培,张澜,梁启超,孙炳文,张耀曾,李济深,韩复榘,毛润之,周恩来;林志钧,张申府,汤用彤,冯友兰。
我研究“学术地图”,就本意而言,不愿也不能仅仅专注“一门学科”,这样,无论视野和胸襟,还是理念和视角,往往与其他人迥然有别,也常常得出『非常可怪之论』。这里,不是标榜自己多么特立独行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,不是有一个词叫“路径依赖”吗?我研究一位学人,不是说看了多少他写的书。也许有人会问:那你研究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?某种程度上,我研究一个人,首先要看是否与我契合,就是所谓契理契机,如果契合,不妨接着看一看相关的回忆,年谱以及纪念文集,那么研究起来就特别的顺畅;如果不契合,不妨放一放!
记得,最早开设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,前几年只聊四位老辈:一,季羡林,二,季羡林老爷子的同事——金克木,三,费孝通,四,王元化,就聊这四位。第一本小册子——《那些有伤的读书人》,有心的学友会看出来,描写季羡林、金克木、费孝通、王元化的四篇文稿,颇为契合老先生的当身际遇、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,尤其是王元化先生一篇,更是如此!这有什么证据?它得到了王元化老辈的首肯。老先生生前审定《王元化集》,第十本是学界对王先生的评议,大概收入了十来篇,谢学友所写《有学问的思想家——王元化先生》,也在其中。
王元化先生早岁住在水木清华,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沪上,自此很少离开上海,一九五五年成为胡风分子,受了多年的苦,受了好多的罪,精神还差一点分裂,再加上,依然承受很重的精神枷锁,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,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。离休以后,等于说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领衔带了几位博士生,上海地区今年高考题目——“专”“转”“传”,就来自王元化先生的一位门生——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以前发布的一篇文章。
再一个的话,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布尔什维克。早期的布尔什维克,比如二十年代的“南陈北李”——陈独秀,李大钊,既是革命者,也是学问家;三十年代沪上,王元化“地下文委”的——孙冶方,和顾准依然有“革命者”和“学问家”的流风遗韵,耳濡目染,长期的地下生涯并没有损毁王元化对学问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我毕业于党史系,因此,内心深处对这些老派布尔什维克有一份别样的温情与敬意。why? 这种情况,就是“契合”。为什么我能够与王元化先生颇为“契合”?不是说读了王元化先生多少著述,而是,更愿意体会王元化先生的际遇和心迹。
后来,不仅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》课上处处有梁漱溟的身影,而且还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上。梁漱溟先生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一块活化石,从东西文化论战到乡村建设运动,从前往延安窑洞探访毛润之到四十年代组建民盟,从反对一化三改到文革期间为孔夫子辩护,再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,简直无役不从。很多学友不无疑惑,谢学友为什么要选择梁漱溟写于1949年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作为《中国文明导论》的本子,根在这儿。
再一个,长话短说,新文化时期,老先生秉持“一分为三”的理念,特立独行,第一,他支持新文化的健将——陈独秀和胡适,支持他们的理念。陈先生和胡先生说,中国需要“赛先生”,中国需要“德先生”,中国需要科学,中国需要民主,梁先生对此,全力支持。这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里面很明确,中国不仅需要科学,不仅需要民主,而且,更需要技术。老先生可以说慧眼独具啊!1978年以来中国的进步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进步,实现了由农业到工业的历史性转型,老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对。
老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,认为传统中国实行的是伦理本位。再一个的话,他为传统说了很多好话,以至于赢得“最后的儒家”之誉。同时,很多人不知道,老先生把传统看透了。传统中国,一个人永远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谈自己——“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,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。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,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,被抹杀。”中国发现不了个人。为什么发现不了个人?家族伦理本位,天地有张大网,谭嗣同先生所说冲决伦理之网罗,所言极是。梁漱溟先生对个人在传统社会生态之中的这个态势看的多么明晰。
我建议诸位学友啊,看书,尽量看一些老辈儿的,梁漱溟先生这样的老辈,1949年之前著书立说,往往在1949年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庶几存在文白相间的情形。不过,只要静下心来,可以突破阅读障碍,获得极大的助益。不说别的,字里行间那股子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,以及议论风生,酣畅淋漓,就让人回味。千万要注意,现在很多课本的主编往往都是知青学者。某种程度上,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,知青学者的气场是铺天盖地的。但是,看他们的书应该有一个警醒,因为自己的脑瓜应该长在自己脑袋上,不应该成为别人陈腐说教的跑马场。教育不是宣传,读书不是传销,一定要注意哦!
可惜了,聊了那么多年的梁漱溟先生谈得上研究吗?谈不上。多年以前,应《新京报》绿茶兄之约,曾给梁漱溟先生写了一封信——《致梁漱溟先生一封信》,关于梁漱溟的很多东西还在我的电脑U盘里边。今年十月退休以后,终于有了闲暇,可以着手整理这方面的资料,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若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来论,梁漱溟属于百年中国的“第二代”。他和毛公,还有张申府,汤用彤,都是同一年——1893年生人。老辈儿波澜壮阔的一生,特别启人心智。
2023年5月程宇静老师主持中文系工作以来,宽容,宽厚,宽和,温暖,温润,温和,发挥所有老师的积极性,让各位觉得,中文系是大家的,连我这个投闲置散多年之人,也被调动起来了。这样,职业生涯临近尾声,两年间带了七篇毕业论文!也许想弥补十年不带论文的缺憾,也许潜意识中把几位学友视为『衣钵传人』,第一时间组建以撰写毕业论文为主旨的『席明纳』,并“定期”和“不定期”进行交流和互动,设若把交流和互动的录音整理出来,相信不会少于二十万字!指导毕业论文过程中,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,整天将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挂在嘴边,“当身际遇,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”也是絮叨不已。
学界怪事多,见惯则不怪!一些专家似乎有着很强的执念,其中之一,就是『毕业论文』的题目必须带有『论』字,否则不像一篇论文!依照这些专家的思路,毛公的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也不符合当今论文的规范,看起来像一篇送别友人的散文!反正我看到——《鲁迅:现代思想史上的“特殊独一人”》这个题目,觉得倍感亲切。为什么?冥冥之中,自有天意,因为我当年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鲁迅,也可以说,敝人与河北科技大学中文系之间,确实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缘。虽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,但是,本人大学毕业论文写的鲁迅,题目叫《鲁迅:荒原狼》,指导老师当然是恩师萧延中先生!
早在去年,我跟所带四位学友商量,能不能独辟蹊径,不从语言风格入手,而是,返璞归真,写一写巴金,季羡林,杨绛,孙犁四位老辈『散文中所呈现的朋友圈』。巴金和孙犁是『文人』,季羡林和杨绛则是『学人』,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曲径通幽,散文创作呈现『井喷之势』,不仅巴金和孙犁晚期的散文有着自家面貌,属于控诉和反省『文革』的『双壁』,季羡林和杨绛两位老辈被孙郁视为『学人散文』的地标。细究起来,『人间重晚晴:论杨绛散文中的亲友圈』,题目最具有灵气,遗憾的是,没用那么大力量,挖掘的不够深入;高艳琪学友所写的《孙犁散文探析:流淌其间的战火硝烟与人间晚晴》,最为踏实,最为努力,最为刻苦,最为勤奋。难能可贵的是,高艳琪学友对“乡贤”——孙犁先生,颇有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,这就为后来写出优质论文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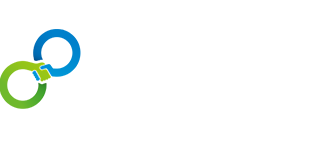
 2025-06-25 20:04:43
2025-06-25 20:04:43 浏览次数: 次
浏览次数: 次 返回列表
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





